2013年5月25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和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院庆90周年•公共管理学术周”主题演讲第11场在五教H5301举行,来自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的E. S. Savas教授发表了题为《政府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Government Do?)的演讲。讲座由国务学院顾丽梅教授主持。
Savas教授此次讲座的内容主要是论述公共物品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合作的方式进行供给,而不仅仅是通过政府来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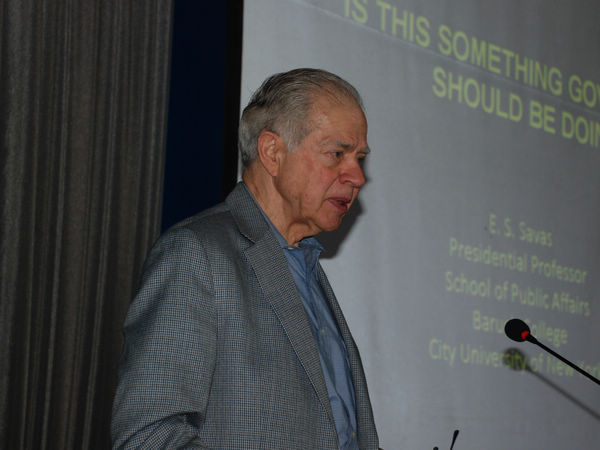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Savas教授首先从公民需求开始,认为在所有社会中,公民一共需要三种物品:有形的物品,例如衣食住行等;实用的服务,诸如是我们免受国内外敌人、犯罪分子、污染、火灾以及毒品等侵害的保护,还有教育以及年老以后的社会保障等;精神服务,例如神父、部长、专家、神学家、巫医、牧师等,还有叔父、兄弟姐妹等亲属的帮扶。
为了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研究,Savas教授对所有物品按照其内在的特性做了进一步分类,即排他性物品和消费性物品。所谓排他性物品是指除非经过供应者和消费者的允许可以排除他人消费的物品,例如日常的市场交易,百货商店中购买商品、电影院凭票看电影,但是排他性实际上是一种程度概念,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成本。而消费性物品则没有排他性方面的特质,既可以被个体性消费,也可以一个群体(无论是否相互冲突的)消费,例如有线电视,她并不会因为有人(无论多少人)消费它而在质量上有所损失,除此以外还有国防。但是汉堡包就明显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一个人吃掉了它,另外一个人就不可能再吃这个,类似的情况还有理发服务等等。但是可供共同消费的消费性物品可能会因为额外使用而产生耗损,比如群体规模可能会损害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像上海博物馆、帕特农博物馆,以及警察和高速公路,实际上这些物品不像有线电视那样,他们并非是纯公共物品。

根据物品的两种特性(排他性和消费性),可以将所有物品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私人物品,包括市场交易物品、婚姻家庭,以及吃穿住行等;其二是付费物品,公共交通和一些非盈利的电影院等等;其三是公共池塘物品,也就是免费物品,例如非濒危物种的野生动物,对于该物品的保护需要通过明晰规则和产权确定予以实现;最后一种就是集体物品,例如国防、防火和监狱等等。
那么在这些物品中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物品呢?所谓有价值物品实际上就是私人物品的交集,比如无论受益人的付费能力如何必须予以供给的物品,像提供给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食物和房子,这些物品所产生的外部性必须是积极正向的,同时可以由政府和社会来予以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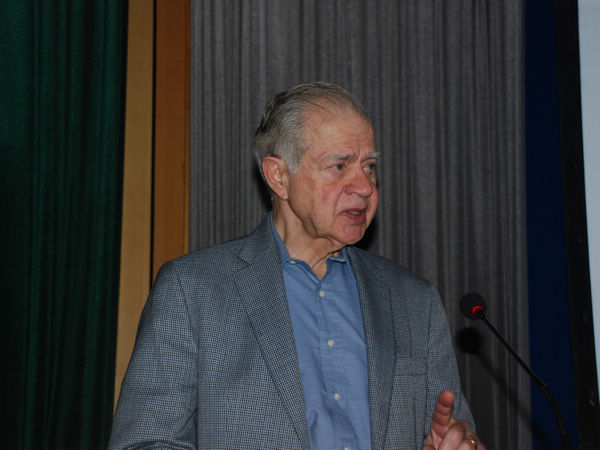
在此基础上Savas教授根据可获得性(feasiblity),即排他性程度,和消费性程度确定了一个二位分布图,而后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诸如打车、钓鱼、公交车、有线电视等等,在二维图中进行了定位。在这些物品的供给中,实际上存在四种组织来分担角色:家庭组织(部落、宗族),供给医疗健康、住房、教育以及其他安全保障;社会,包括各类的志愿者组织、社区组织、教会、慈善组织、邻里组织、协会、校友会和各类专业化组织等;市场,存续了几千年,堪称供给私人物品的最有效途径;政府,在20世纪不断增长的对集体物品的需求中,政府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也正因此,政府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挤压了其他三个组织的活动空间。
将四类组织与四类公共物品的供给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发现家庭组织的物品共计更多地集中在个人物品上,例如情感与身体安全、儿童抚养与教育、家庭成员互相支持等等,社会则可以供给四类物品,而市场则集中供给私人物品和部分的付费物品,政府则需供给四类物品,既有基础教育和医疗在内的个人物品,又包括最为广泛的野生动物保护、污染防治等纯公共物品,同时还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付费物品等等。

但是最后Savas教授的关注点主要放在了政府的角色上,因为政府负担实际上已经是超载,20世纪,政府承接了太多的职能,以至于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大量的制度性资源实际上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被消耗掉了。最后Savas教授将政府已在担负的职能分为三类,不应承担的职能,对于这一部分职能政府部门应逐步的退出、出售、清偿或者私有化,让私有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承担的职能,政府部门应该集中精力专注于这些内容,改进管理质量和下放管理层级,以及必要的公私部门合作;可以承担的职能,对于这一部分职能,如果第三部门有能力承担则尽量交由第三部门承担,至少也应该通过公私部门合作的形式完成。
(CCPDS 王军洋 供稿;国务 审校)


